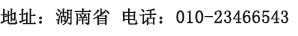曹公笔下的宝钗是个端庄温和、博学多才、孝顺通透的女孩儿,绝非偏心黛粉们解读出来的阴险狡诈的白莲花,“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当有人戴上美品滤镜的时候,必然有人会被泼上脏水。这次我们开始掰扯掰扯偏心黛粉们给宝钗身上泼的脏水。
89版电影宝钗扑蝶有人把滴翠亭偷听事件当做宝钗阴险狠*,陷害黛玉的证据。其实是宝钗来不及躲开,用一个伪证人证明自己没有偷听。曹公用宝钗的心理描写明明白白地说她不想惹上麻烦,薛家在贾府是比林黛玉更远的远亲,所以宝钗一直秉持知分寸守分寸的态度与贾府相处。她对亲表姐王熙凤都尽量疏远。有人说她称呼凤姐为凤丫头为不知礼,错!她和凤姐是亲表姐妹,又寄人篱下。素日虽然常怀嫉妒之心,不忿凤姐宝玉两个,也不敢露出来的赵姨娘之流无凭无据尚且敢说:“提起这个主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如果宝钗和凤姐接近,那流言蜚语更是不知传成什么。宝钗既不称凤姐嫂子,也不叫姐姐,就是模糊她们的亲戚关系。加上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这正是薛家自立自重的表现。没想到书中的“嫌隙人”没有生出“嫌隙”来,书外的“嫌隙人”花样百出地生出让曹公都想不到的“嫌隙”来。
赵姨娘继续说宝钗偷听,这完全是偶发性事件,宝钗去找黛玉,见宝玉先一步进了潇湘馆,宝钗转身回来时看到一对蝴蝶,宝钗扑蝶误打误撞到滴翠亭,听到小红和坠儿的对话。没有预谋,完全是随机性的。其次,这件事后没人再提起,如果宝钗真的像偏心黛粉们臆测的那样,她不应该以此为要挟,让小红听命于她吗?或者泄露给别人标榜自己的知礼受礼吗?又或者义正辞严地训斥小红一顿,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吗?她全没有,她转身离开后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了。
87版电视剧宝钗扑蝶这样一件小事儿都让偏心黛粉们过度解读成栽赃陷害,那咱们就掰扯一下栽赃陷害。第五十八回,藕官在大观园烧纸祭奠药官,被夏婆子抓住要回王夫人去,被贾宝玉拦住,说是藕官烧纸烧的是受了林黛玉的支使,夏婆子拿出没有烧完的纸揭穿贾宝玉,贾宝玉又扯谎说是他支使藕官为他烧的纸钱,最后和夏婆子达成和解推说藕官被黛玉叫走了,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并没有完,到第六十回,夏婆子怂恿赵姨娘的时候说:“我的奶奶,你今日才知道?这算什么事。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宝玉还拦在头里。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就说使不得,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这烧纸倒不忌讳?……”如果宝钗只是撒谎,贾宝玉这算不算是实打实的栽赃呢?而且因为这件事,夏婆子记仇,借芳官用茉莉粉换了蔷薇硝的事儿怂恿赵姨娘大闹了一回怡红院,后果远比小红担心要严重吧?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第四十六回贾赦想娶鸳鸯,邢夫人想让平儿去说和,凤姐怕牵扯其中,让平儿去园子里逛逛。在丰儿扯谎说平儿被黛玉请去了,凤姐还故意说:“天天烦她,什么事儿啊?”凤姐用黛玉扯谎对的可是邢夫人,就算是王夫人见了邢夫人也要客客气气地叫一声嫂子的。而宝钗扯谎针对的就是怡红院三等小丫头小红。这两件事也都是借黛玉扯谎,和宝钗扯谎一样都没有什么恶意。为何他们扯谎的事儿没有像宝钗扯谎那样上纲上线到栽赃陷害和质疑人品呢?如此双标是正直还是对宝钗恶意解读?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下面再说一个有恶意、有预谋、有严重后果的实实在在的栽赃陷害——夏金桂对香菱的栽赃陷害。第七十九回写夏金桂“他母亲皆百依百顺,因此未免酿成个盗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曹公用旁白明明白白告诉读者夏金桂人品就有问题。“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是动机,后来叫人以取帕子为由,让香菱误闯薛蟠和宝蟾偷情现场,后来又用巫蛊小人污蔑香菱害她是手段,害的香菱挨打,后来“把前面路径竟自断绝。……今复加以气怒伤肝,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饮食懒进,请医服药不效。”为“致使香*返故乡”做下铺垫。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诬陷。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那些偏心黛粉们把宝钗那句没有预谋、没有恶意的谎言当成诬陷,却对上面所提的三人三事极少提到,他们本人不觉得怎么,但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人不以事实为依据,妄加猜度,恶意解读,让好人的日子过得格外艰难。这种人真的面对恶人的时候他们又用宽宏大量粉饰自己的懦弱无能,纵容恶人。这就是所谓“让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让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