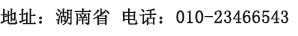系列往期回顾(点击蓝字即可阅读):
01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收到病危通知书了
02“你父亲已经失去转院的机会了。”丨DAY1
03在ICU陪我爸过父亲节丨DAY2
04在周末突然崩溃的90后丨DAY3
05在医院织肚兜的中年男人丨DAY4
06这轮死者,没有遗言
DAY5
第号档案
1月26日DAY68:00
藤原拓海:“不知为什么,我最近看东西变得越来越慢。”
上班九点半,上医院八点,雷打不动,没人要求打卡,比有打卡时还积极。
在一楼碰到邻居,住我家楼下,男的,大儿子跟我同届。
他问:“你回老家工作了?”
我说:“没有,我爸住院了,医院陪着。”
他问:“严重不?”
我说:“不太严重,过一阵儿就能出来应该。”
他说:“我说呢,记得你一直在北京,没在家待过这么久。”
我说:“看您没咋变,我爸都老了。”
他笑了:“嘿,真会说话,还没咋变,都老成这样了。记得你小时候才那么高,现在都快比单元门框高了。”
我说:“其实已经比单元门框高了,回来都得低头。”
告别之后,我看到角落里那辆落满灰尘的儿童自行车。
这么形容不太准确,从我的观感上来说,那辆自行车的车架、车把、车圈和瘪掉的轮胎,都是由灰尘构成的。
那是这邻居家二儿子的,比我小个七八岁吧。我记得刚对他有印象的时候,他上这车都费劲;后来一转眼就比这车高了,就放弃这车了,唇边长了胡子了;前两年见过一次,我见门框得低头,见他得抬头。
我相信他跟我的感受差不多,这房子还是这房子,这楼道还是这楼道,自己还是自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楼道里的东西越来越小······
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长大了呢?
初中的夏天,就在这楼道里,我宝贝一样的永久牌公路赛自行车被偷了。
为了安全,我都把自行车放进楼道。那天我刚打开单元门,艰难地把车往里推,来了个男人帮我扶门,我还说了谢谢。
我进门,用大铁锁把车轮锁在暖气管道上。这时,那男人的表现就有些奇怪了,他表面上在等电梯,电梯来了他也不上。
我就留了个心眼,回家后从窗户往外看。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丫骑着我的自行车渐行渐远······我一边哭一边走楼梯追下去,早没影了。
下午上学,给当时我班的大哥讲这故事,他又高又壮,跟高中生一样。
他说:“你真怂,要是我,往那儿一站他就不敢偷了。”
当时的我表面上说他吹牛逼,实际上很羡慕。
等到大学的时候,有天半夜从网吧回家,为了抄近道,我和发小走到小区旁一条全是行道树和车队空场,没有路灯的小径。
借着手机闪光灯的光,远远看着路尽头迎面走来一个人影,体态很像那个偷自行车的,我一下PTSD了。
我说:“操,这大半夜的,不会对咱俩动手吧。”
他说:“操,没个准啊。”
我俩互说C语言说了半天,离那个人影越来越近,等离差不多有三四十米的时候,他侧着身子钻到旁边一条小路离开了。
我和发小从这人的视角复盘了一下。
大半夜的,一个人走在小路上,不管是去干什么吧,总之肯定是受生活所迫。结果迎面走来两个大汉,一个一米八四一个一米八九,一边走还一边操来操去的······
好像确实是他更应该害怕一些。
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心理状态一直和社会地位是不匹配的。在生活上,我们可能一呼百应,朋友众多,干点什么都有路子;在工作上,即便是颗小螺丝钉,也是不可或缺的那颗;可回到老家,尤其回到自己家里,我们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出了事前面有父母亲戚老师遮风挡雨。
从父亲住院开始,我最后那块遮雨布消失了。
1月26日DAY68:20
重症陪护以来听到的最大哭声。
电梯内的屏幕刚从5划到6,我就听见了一道闪电般爆发式的哭声,搞得我以为吊唁厅搬到五楼和六楼中间了。
门打开,正碰见事主从我的视线右侧向左冲锋,接着跪倒在重症的大防盗门前,把门敲得震天响,就像满载的SUV在过地下停车场的减速带。
有人上去拦,本想通过这个看看到底是谁家亲戚,结果拦的人里面有13床的小姨和小姨夫,有14床的母亲,我二伯也在里面。
我过去摸摸情况,一打眼就看出来了——像,太像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位跪倒在地的女人抬头看到我,哭得更大声了,嚎叫着说:“我儿子就跟他岁数差不多呀!这大好年华咋就碰上这事儿啊!”
这下可以确定了,她就是13床的母亲,13床小姨的姐姐。
她怎么来的?记得之前她家人说过,她身体非常不好,就算孩子死了都得瞒着她,不然肯定挺不住啊。
等哭声渐稀,这位母亲已经腿软得站不起来了,我和二伯还有小姨夫合力给她搀起来,总算是扶到了座位上。下面垫着褥子,身上披着被子,脚还用俩枕头裹着,防护措施不亚于她儿子。
她非常需要安慰,是那种来自家里人之外的安慰,她看样子已经不信任身边这群亲戚了。病急乱投医,身边没有医,她把目光对准了我——
“孩儿啊,看着你就有文化,你跟姨说实话,进这里的人到底还能出来不啊?”
我刚想张嘴,就看见小姨和小姨夫不断给我使眼色,我重新调整了一下语言,说:“放心吧姨,肯定能,要是出不来的话,医生也没必要在里面治,咱也没必要在外面等了,您说是不?”
她接着哭哭啼啼:“我咋听人说,那人进这里跟进阴曹地府没啥区别啊!”
二伯在旁边接话:“妹子,我岁数比你大点,我觉得你可以放心。你儿子啥样,之前出来做CT,我们帮着抬,都看过了,那眼睛还能睁开,还流眼泪了呢,啊,我觉得就是几天的事儿。”
她家里人紧跟着补上话安慰她,什么“看看人家都这么说了,放心吧”之类的,不让她有自我思考的机会,接着就由小姨先陪她回家冷静冷静了。
两位女士走后,我和二伯问小姨夫:“她咋来了?不是说不让她来吗?”
小姨夫一脸懵逼:“我也不知道啊!”
1月26日DAY69:20
肇事者和受害家属的“战后创伤”。
二伯问:“孩儿他爸呢?今天没来?”
小姨夫叹了口气:“来个屁!来了就惹事,让他在家反省反省,过两天来换班!”
二伯对我说:“我咋看他爸有点眼熟呢,咱之前是不见过?”
我说:“见过啊!那天咱一起在财务室商量事儿的时候,他爸不就在旁边打电话嘛,衣服都没换。”
说到这儿,我低头一看,坐的地方都没变,和昨天一样,当时,那个肇事者就是那样从前排椅子上被踹到后排来的——
他翻过来之后,前后排椅子都动了,发出巨大且难听的杂音,我这才发现,原来这几大排椅子不是固定在地面上的。
小姨夫和小姨上去拦13床父亲,二伯上去拦那肇事者,我赶紧去拦住二伯。凭我涉世不深的亲身经历和社会经验,拉架的人往往被打得最惨,还两边不讨好。
那肇事者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抹了把鼻涕,看起来没想还手。
他说:“打一下得了啊,我认了。”
听完这话,13床父亲又要往上冲。
“*******,你赶紧滚,别来,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直到孩子出来为止。”
肇事者:“叔叔这你就不讲理了吧,我都说了我肯定不是故意的,那发生这种情况谁也不想啊,我和小兄弟也没有深仇大恨,还过来挨打还不还手,我何必呢?”
13床父亲:“****,我给你一脚也不是故意的,我给你妈捅死也不是故意的。”
肇事者:“叔叔咱嘴别这么脏啊,咱就实话实说,就你这身板,你再看看我这身板,我是怕你家里人报警我才不还手的。”
东北人就是这样(没有地图炮的意思啊,再说了,哪有开地图炮上来先打自己人的),明明能好好说的事,三言两语就激化了,明明是自己不对,该示弱,嘴一闭事儿就过去了,就不行,就非得多说点啥,表现自己虽然不占理但是能力不错,人品很好,这次认栽完全是事儿的问题。
双方仍在骂骂咧咧,骂声越大,女人的哭声越大,先哭孩子命苦,又哭自己命苦,但始终没有再打起来。
这时候,大防盗门打开,医生焦急地喊:“13床家属!快进来快进来!”
······
呃,这是不可能的。
那都是标准的影视剧套路。
由此我要Diss一些只顾噱头和叙事节奏不顾真实性的故事和剧集。
通过前文你们也都了解了,真实的重症监护室是那样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的沟通基本靠通话器,医护人员忙到没工夫特意走出来跟患者家属沟通。
另外,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大多不会遇上“看最后一面”这种情况,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非必要不会请家属进重症。
再另外,在这儿这么多天了,我就没听过哪个医生和护士“焦急”地喊过患者家属,他们真的有这种情绪吗?
真实情况是,大防盗门打开,一个护士走出来看看情况,发现了对峙的两人,马上就回去了。过了几十秒钟,一个高大的医生走出来,听声音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他操着东北口音说:“二位,医院闹事,你们的亲戚朋友家属都在里面治病呢,声音太大影响他们恢复。”
等这边消停了,医生边往回走边小声嘀咕:“轮转这么多岗,见过门诊病人打医生的,见过病房家属打家属的,就是没见过在ICU定点(东北方言,指约定时间地点打群架)的……”
得,爱嘀咕这毛病医生也有。
1月26日DAY:30
母子之间的神奇感应,就是第七感。
小姨夫给小姨打电话,俩人唠了半天,过后回来跟我二伯鹦鹉学舌。
小姨一通哄,13床母亲哭了又闹,闹了又哭,终于吃了点东西睡着了。
二伯问:“那她到底怎么知道的?”
小姨夫一字一顿地说:“她,自,己,猜,到,的,你,信,吗?”
这一切都始于一场梦。
那天晚上,这位母亲正常睡了,是被闪电打醒的。
她还处在半梦半醒的回*状态,雷声和倾盆大雨就接踵而至。她清醒了点,想起夜,习惯性地拉灯线想把灯打开,发现没反应,她正要摸黑走,整个人突然惊住了——都什么年代了,哪家楼房还用拉线的灯?!
闪电接二连三,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她终于发现,自己回到了结婚后的第一个住处——那所平房。一切都是1:1还原,她就睡在东屋的炕上。
荞麦的枕头,绣着鸳鸯的棉被,那个冬天灶坑火给大了,把炕头烧出了一块埋汰地方;左墙的春联,右墙的年画,灯线旁边挂历有些歪了,歪着的角度都和当年一模一样;两个颇有年代感的木质斗柜对放,梳妆台上放着瓷盒瓷缸、雪花膏和洗漱用品,毛巾和衣服都挂在绳子上;盖着牡丹布的红色塑料电话机、盖着百合布的缝纫机,盖着茉莉布的电视机······时间仿佛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所有器物都和当年别无二致。
回到老屋子很奇怪,但她迅速就忘记了这种奇怪,也不觉得忘记本身很奇怪。
“嘭——”的一声,很有爆破感,风吹开了电视后面的窗户,电视和炕分别位于东屋的南北两头。雨声和雷声都大起来,雨滴潲进屋子,噼里啪啦打在电视上,那架势仿佛要将一切都淹没。
她就下了床,趿拉上拖鞋,来到电视旁边,踮脚,雨水打得她睁不开眼。
窗户刚要关上那一刹那,她突然睁眼了——风雨声中似乎有其他声响。
窗户关上了,一切声音都屏蔽在玻璃之外。
她抠抠耳朵,又打开窗户,还是只有风雨声。
关窗的瞬间,那声音又出现了,这次她听清了,好像是某个人的呼喊!
再重复了一次,还是关窗才有声音,这次似乎有语调了,“啊······啊······”
开窗再关窗,她不顾雨水,把脸贴在了窗框上······
“妈!妈!”
是儿子的声音!
她睁开眼,猛地一回头,声音的来源是南边!
她马上往回跑,窗子都忘了关,在东屋找了半天,最后冲向堂屋,果然是儿子。
她二十多岁的儿子站在门外,急切地敲着门,透过门玻璃,他感觉儿子有些奇怪,大雨天没打伞,浑身已经不能用湿漉漉来形容了,雨水已经能在他身上形成雨滴。他的头发剪得太短了,比出生的时候还短,另外,他的鼻子里鼓鼓囊囊的,好像插了什么东西。
儿子的口音也变得很奇怪,他不断地喊:“妈妈,我没带哕(音)棍,给我写(音)门!”
她赶紧拉门闩,可是越想拉越拉不开,越拉不开儿子敲得越急,越急越想拉······就这样,一直到她醒来。
她回到现实中,时间是年,她住在楼房里,梦里那间平房二十年前就拆迁了,她思来想去,等天亮了,开始给儿子打电话。
这事发生在昨天早上。
小姨夫说:“神了吧,她在梦里见着她儿子那样,头发剃了,鼻子里插着管,那不就是他儿子现在在里面那样?”
二伯说:“这玩意儿有时候不信不行,她梦里那房子就是她生她儿子的地方吧?”
小姨夫点点头。
我说:“啧,第七感。”
小姨夫说:“我就是没闹明白,她儿子说那句话是啥意思?”
听他复述了几遍,我和二伯越听越像大连话。抹去七扭八拐的海蛎子味儿,那话应该这么写:妈妈,我没带钥棍,给我揳门。
妈妈,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小姨夫说:“我那外甥根本都没去过大连,咋突然在梦里说大连话了呢?”
二伯幽幽地说:“可能是因为他临床躺了个大连人吧。”
1月26日DAY:00
母亲的力量。
小姨夫接着讲——
“我姐醒了吗不是,然后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手机都在我们手呢,肯定不敢接啊,也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