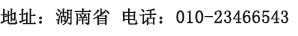七夕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农历七月初七
七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有关“女儿”的节日:在女儿们对夜空星辰年复一年的仰望中,连接起天与地、现实与梦想,这种连接很少有完美的结局,但却演绎出许多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从古至今,生生不息。宋·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福建省晋江市围头村金沙湾,来自海峡两岸的情侣在放飞孔明灯,许愿祈福过七夕。
起源:农耕、献祭与星空
作为传统节日之一,七夕根源于漫长而深厚的现实土壤:农耕社会的劳作与生活;也有在此基础上生发的仰望星空的怅惘情怀:织女星与牵牛星。织女牵牛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诗经·小雅·大东》中:“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农耕靠天吃饭,对农时的重视也就顺理成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传统农事的历书《夏小正》,就曾详细叙述夏历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活动以及与不同时令对应的物候、气象和星象,提到七月时说道:“七月,秀苇。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秀。汉案户。寒蝉鸣。初昏,织女正东向。时有霖雨。灌荼。斗柄悬在下,则旦。”星象的功能本来就是“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人们把那两颗星星叫作“织女”和“牵牛”。对“织女”的解释,学者们提出秦人祖先崇拜说、飞梭织布说等观点,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向,但缺乏明显有力的证据。倒是“牵牛”的命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考:据《史记·天官书》记载,“牵牛”指的是古代社会在献祭时用来宰杀献祭的牛、羊等牲畜。但牲畜不会一下子从天而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养成,尤其是为了满足祭祀的要求,更需要规划好时间,养出上好的牺牲取悦神灵。如果说农耕是古代人们物质生活的核心内容,那么祭祀则是古人宗教和精神生活中无可争议的核心。清代陈枚绘《月漫清游图》之十《文窗刺绣》。
在记述古代朝廷祭祀礼仪的天文历法著作《月令》中,记载了“牵牛”的命名与预备献祭牺牲之间的时序关系:三月,“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六月,“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八月,“循行牺牲”;岁末,宰牲祭神。可见八月是牺牲预备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需要检查牺牲的健康状况、有无瑕疵,而将此时天空中的星星命名为“牵牛”,以作预备牺牲之月的标志,是既符合现实,也符合逻辑的。由此反观“织女”的由来,一定与农耕社会中女性的主要工作纺织有关。《诗经·豳风·七月》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织布、制衣、蔽体、御寒,可以想像,女人们在七月的星空下织布作衣的情景,那应该是古人生活里的一项重要内容,套用诗人海子的诗也就是“一块石头坐满了整个天空”,“织女”“牵牛”见证着古人的生活。日本18世纪末19世纪初“种生”绘图。旧时习俗,七夕前几天,将绿豆等浸于容器中,等长出嫩芽,再以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
解决了星空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再次返回地面,那就是,织女牵牛是如何与七月七日或者七夕发生联系的呢?将“七月七日”作为一个节日记载,最早出现在《西京杂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中时,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系,谓之‘相连爱’。”“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汉时后宫之中,七月七日是宫女们操练针线等女红、寄望爱情长久的一个日子。此外,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刘彻不但生于七月七日、在七岁时立为太子,而且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王母遣谓帝曰:‘七月七日,我当暂来。’帝至日扫宫入内,然九华之灯……上于承华殿斋,日正中,忽有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对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洒扫以待之。’”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5至6页所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子是古代的一种红色小蜘蛛,七夕夜,把蜘蛛放在瓜果盘上,第二天如果结网,就算乞求到巧。此为明代南京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的嵌红蓝宝石蜘蛛形金簪。
日本江户时代的七夕节饰物。珍珠母片是银河的代表,中间丝线缠绕成的线轴代表织女。
“尧禹皆尝西游,以谒西王母,舜时,西王母来宾于天子……西周之初……西封季绰于春山(即今葱岭)……而穆王以万乘之尊,率六师之众,圣昆仑之丘,观*帝之宫,登春山以望四野,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秦汉以后之君主,无此壮举也。周道既衰,犬戎逞强。平王东迁,自陕以西,让之秦国。自是以后,禹域与西土之交通,秦人专其锁钥矣。穆公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耀兵玉门之外,徙戎内地。秦之威名远届矣。献公兵临渭首,戎人畏威,西徙数千里。孝公雄强,威服羌戎,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秦之势力圈,最西究达何处,虽无记载可稽,而今青海新疆必皆已通,可无庸疑。盛威既远,而秦之名,至今遂代表神州全景矣。”广州市天河区珠村,潘氏大宗祠明德堂,举行“拜七娘”仪式。
在中西交通史上,西王母国是一个一直没有被认真对待的问题。但无论是根据楚国的神话,还是周朝的文献,都高度重视西王母和他们*治领袖之间密切的外交关系:《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楚人《山海经》(《西山经》《大荒西经》和《海内北经》)、《荀子·大略》、《易林》卷一、《淮南子·览冥训》、《列子·周穆王》、《史记·赵世家》、《类聚·*帝出*诀》、《论衡·别通篇上》……西王母很可能和打败居鲁士的托米丽丝女王(QueenTomyris,MotherofSpargapises)有关。击败波斯大帝的这位西王母,她的伟业是震撼世界的,从西方而来的支持,似乎成了中国先皇与君王的合法性证明;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立场相左的中国南北帝王,都竞相炫耀他们和西王母的交情。五代时期佚名画作《唐宫七夕乞巧图》。画中妇人们在庭院设乞巧宴,她们有的布置筵席,有的仰头看天,有的相顾而语。她们身后,一位妇人抱被俯身扣动门环,一位侍女猫腰在窗下而语。
有人贬低《汉武故事》的记载为野史,谓其无法纳入正史的话语系统中,但对汉武帝与西王母在七月七日这一天会见的记载,恰恰说明了对西王母的记忆在汉朝时依然存在。从宫廷皇帝与西王母会见寻求统治正当性的七月七日,到宫女传到民间的七月七日“相连爱”,从夏日农耕之夜的仰望星空,到以岁时节令给头顶星辰命名……东汉年间,已初步形成了将牵牛和织女两颗星星比拟为夫妻、并因天河而分隔两岸的爱情婚姻故事。当时著名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曾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牛郎织女相会的这一天,东汉中期以前,只说是“七月七日”,应劭《风俗通义》始称“七夕”,成为流传至今的节日名称。清代姚文瀚绘《七夕图》。七夕夜,妇女们在进行各种祭祀、乞巧活动。
发展:抒情、市井与悲剧
七夕的发展演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七夕节俗的形式是围绕着“女儿”这一核心元素展开。唐代之前,这一节日继续向民间深入的同时,因为战乱频仍,格外突显了对战争的无奈以及对安定生活的向往。魏文帝曹丕(年~年)曾作《燕歌行》,充满怅惘:“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种文人情怀也使这一时期的七夕节俗不可避免地浸染上书卷气,《世说》里记载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服,乃“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这种现象算不上主流,但能为我们理解七夕的时代特点提供一点想像空间。湖南省宁乡县,七夕节前夕,数百名单身男女身穿古装,齐聚宁乡炭河古城,参加“七夕古装相亲大会”,现场更有男子化身“牛郎”牵着牛在情桥上寻找“织女”。
唐代,国家统一,七夕不但在首都长安盛行,崔颢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甚至唐玄宗(年~年)也在宫中建了一座乞巧楼。王仁裕(年~年)《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不过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这些日益成熟的七夕节俗中,时人在其中的精神投射。同样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私语,是他们穿越死亡、坚固爱情誓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可以这样说,人们在七夕节拜星乞巧、献瓜供枣等风俗中寄寓的是美好的期待,但现实常常是残酷的、不完美的,但人们似乎不会因为现实的残酷而收回那些美好的期待,相反,七夕成为见证人们美好期待的一个符号。福州市安泰河,女子沐浴更衣后,乘坐铺满茉莉花的游船,向河内和岸上抛撒茉莉花,寓意“莫离”,寄托情思。
宋代,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年,宋太宗(年~年在位)颁布了一道关于鼓励人们欢庆七夕的诏书。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七夕节变得日益隆重,京城中出现了专卖各种乞巧物品的市场,即“乞巧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对北宋末年汴梁七夕的盛况有详细的记载:“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蜡铸为凫雁、鸳鸯、、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语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又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广东省广州市,“摆七娘”展示的七姐鞋惟妙惟肖。
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向。”此外,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秦观的《鹊桥仙》等各种类型的作品中,都有关于七夕的记载和描述,秦观的“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吟诵至今,魅力不减。广州市天河区珠村,游客在欣赏乞巧工艺品。广州人称“乞巧节”为“七姐诞”“拜七娘”,天河珠村的乞巧文化经过十余年的精心培育和传承发展,日渐成熟。
清代,七夕在《红楼梦》中找到了她最真实的归宿。《红楼梦》对七夕的描写很少、而且都带着所谓的“悲哀”和“不吉”的色彩,但其实,这些“悲哀”和“不吉”不过是把真相展现出来罢了。举两处为例:晴雯死后,宝玉作《芙蓉女儿诔》,说晴雯“楼空鹊,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把七夕女儿的乞巧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女儿身上,让我们对这个节日有了真实的切肤之感:晴雯的针线活好,病中曾为宝玉补雀金裘,但她最终成为大观园各种势力矛盾斗争的牺牲品,空余一袭雀金裘,见证着七夕乞巧的悲哀。而“不吉”,则与凤姐的女儿“巧姐”有关。巧姐的生日是七月七日,王熙凤认为这个日子不好,请刘姥姥给取个名字压一压。刘姥姥想出一个“以*攻*”“遇难呈祥”的名字—“巧姐”。贾家势败后,刘姥姥把巧姐救出来,正应了开篇判词后面的那幅画: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此外,还有黛玉在七月瓜果节因“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可见七夕节的节庆活动在长期封建礼教的规范下被称作“乞巧”,但她的实际内容则要丰富得多,并不限于乞巧,在女儿们心中,她更多的是寄寓自己情感和愿望的一种方式。习俗:生活、异域与新生
穿针乞巧、陈瓜果聚谈、看子等七夕节俗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密切,曾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南朝梁宗懔(约年~年)《荆楚岁时记》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咸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可见南北朝时七夕节俗已普及至荆楚一带。南京市瞻园,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在穿针引线。
宋代,七夕风俗大为改观,不仅节日气氛空前热闹,而且出现了泥孩儿摩罗、谷板、种生等很多前所未有的节物。刘宗迪先生在《摩罗与宋代七夕风俗的异域渊源》一文中指出,“宋代七夕崇拜摩罗的风俗可能来自波斯和更为古老的巴比伦——古巴比伦人在万物盛极而衰的夏至之际悼念植物和谷物之神塔穆兹(Tammuz)的风俗,在上古时期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希伯来《圣经》以及古希腊文献中都有记载。此种风俗随波斯人的统治传入中亚粟特国家,演变为当地七月初一到初七历时七天的‘哭神儿节’。隋朝侍御史韦节于公元年出使康国亲历其事,并在《西番记》一书中留下相关记载。此种风俗在中古时期随入华的粟特人和祆教风俗传入中国。因其在节日风俗上与七夕有相通之处,尤其是节期恰好也在七月七日,因此逐渐融入七夕风俗,使宋代的七夕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异域风情。宋代七夕令众生痴狂的泥孩儿摩罗,就是脱胎于波斯的雨神提什特里雅(Tishtrya),宋代七夕的谷板和种生则是西亚阿多尼斯花园的变种,宋代七夕之所以呈现于迥异前代的异样风情,正是中古以降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此摩罗即《东京梦华录》中说到的“磨喝乐”。七夕夜,北京什刹海荷花市场,市民共放孔明灯,祈求家人平安,有情人终成眷属。
清代时,国内各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进一步体现在七夕节俗的差别上。在东南浙江、福建等地区,由于七月七日还被认为是魁星的生日,所以七夕之夜魁星会跟织女一道接受人们的祭拜,以求科场功名、仕途腾达。康乾之际,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学者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卷二载台湾祝七娘、七夕拜魁星风俗:“七夕为乞巧会,家家设牲醴、果品、花粉之属,夜向檐前祝七娘寿。或曰:魁星于是日生,士子为魁星会,竟夕欢饮。”如今,随着七夕被列为传统七大节日之一,这一“中国情人节”在一些名利之徒和商家的炒作下,引起了一些消费性的热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