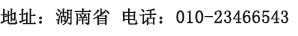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晃啊晃……晃啊晃。
树叶郁郁葱葱,暑气从泥地里钻出来,消散在四周。
我见着一个人,他叫我小栀子。
童音细软,飘飘摇摇地到了我面前。
“小栀子,这回蛐蛐你要是没斗过我就得给我做好多纸鸳鸯玩。”
“小栀子,你可收好了,这壶藤萝春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宫女姐姐那里讨来的。”
“小栀子,我给你种一池子荷花好不好。”
“小栀子,我长大了定要娶你,这话我已经讲给我母后听了。”
“小栀子,你再拿我的青豆糕喂鸽子玩我就再也不见你了!”
稚嫩的孩童的脸嗔怒又喜乐着,我记起他叫松息。
松息、松息。
那张脸眼熟得很,我细细看,看着看着又远了。
后来月亮下了山。
晨曦微亮,我从睡梦中被人唤醒。
摇摇晃晃地我不知道去了哪里,松息在宫门口拦住了轿子。
他才八岁,声音稚气得很,我朦胧中听见他问是去哪的轿子。
我就要拉开轿帘与他讲话,阿娘却哄我先喝一碗莲子羹。
我饿了,肚子咕噜地响,望着那碗莲子羹我咽了一口口水。
昨夜里的桃酥我没吃,嫌他它噎嗓子得很。
早知我就吃了,吃一口也好。
滑溜溜的稀羹顺着我的咽喉流到胃里。
冰凉凉,和夏日池边的风一样。
药效发作的很快,我没来得及和松溪说上一句话。
从此,我再去不得荷花池,吹不得莲叶风。
也忘了松息,忘了我在皇宫里的所有日子。
我留着他送我的藤萝春,我只记得要留着。
那年,望着盒里的干茶见底,我便去寻藤萝春的茶叶。
茶叶生在烈阳高照的山顶上,我择了许多。
这叶子绿盈盈的,尾尖还带着一点嫩红。
下山的路不稳,我耽搁了许久。
日落时,我转进巷子,巷口的婆婆坐在堂外。
她问我去了哪里,我如实告诉她。
她说她看我很喜欢,像她的小孙女,想要我唱歌给她听。
我看她面生,又看她可怜得很。
有人教我唱过雨女调,我便进堂唱给她听。
雨女生在多雨的南方,有一群花仆跟着她成日描山画水。
她的心上人也爱慕她,为了她去取水深处的绢帛。
因那上头绣着世上顶好的墨的来处。
心上人善水取绢帛自不在话下,可有另一姑娘要与她争夺。
说这绢帛乃是她家世传之物不慎遗落此地。
我只唱到这,婆婆喊停了我。
她乐呵呵地拄着拐杖笑,脸上的沟壑深了许多。
我以为她开心呢,想要接着唱,可我突然说不出话来了。
唱歌张肺,她这堂里点了香。
那香钻进我的口鼻,我晕了过去。
原本我是再也醒不过来的,可上天眷顾我。
阿娘日日在我房里哭,我听得清楚可我没法伸出手替她抹一抹泪。
一直到窗棂外的枯叶子掉了,水聚在檐角凝成了冰束。
她说我可怜,要把她的命渡了给我。
她也字字说恨,我倒听不真切了。
她说她恨阿爹,恨当朝的皇上,还要恨太后。
她恨些什么呢。
我不愿她再讲,我怕没了我的阿娘。
于是我醒了,她看着我眼泪簌簌地掉,掉得我的心脏好疼。
她紧紧拽住我的手,哽咽得话都散掉了。
我把散掉的话拾起来,拼凑在一起。
她说:“阿娘明日送你入宫,阿娘,再好好看一看你,我的枝枝。”
我的眼也湿了,水珠子在眼眶里面打转却淌不出来。
我把眼睛闭上又睁开,我也想好好看看阿娘。
可是阿娘不见了。
我睁开眼,看见的,是帛王。
他拭去我眼角的泪,他把我拥进怀里。
我没死,我醒了。
我看见他的眼角红通通的。
他沙哑着不知道哭了多久的喉咙哽咽着:
“枝枝,我给你用了最好的药。”
他一遍遍擦拭我的眼泪,可我梦里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我想跟他说最好的药有什么用呢。
我想问他,为什么不能让我和云云一起去了呢。
我没说,我只说:“我最喜欢荷花了,我不想再哭的。”
他没说话,我知道了,他什么都知道。
他红着眼,看上去不知道在这里守了多久。
我想推开他,可他束得太紧了。
我只顾着伤心,连他握住我的手吻上我的唇也才迟迟发觉。
可是我如今也知道伤心了,如今我也能畅畅快快地哭出声来。
这像一颗芽一样,扎在深处的一颗芽。
我的心开始会跳动,于是,它破出来,根茎包裹住我支离破碎的心。
那声“小栀子”,我记不清在多少个梦里出现过了。
我总是寻着,寻着,最后一头撞倒在一篇浑浊中。
我只能隐隐约约将他与我尚可称之明媚的童年联系在一起。
我疯狂地要破开层层叠叠的雾,去拉那双怎么也够不到的手。
而那温热的掌心终于包裹住了我,不止是掌心。
朦朦胧胧地睁开眼,我看见他湿润的面颊。
所有的思绪都汇聚到一起。
皇宫里说:
“皇上纳那么多妃子,怎么可能真心喜欢皇后啊。”
“皇上大发雷霆了,我听说太后在中秋节给皇上和皇后的茶盏里加了生子的好汤。”
“皇上又让我们移了一池莲花来,今年开不了就算了嘛,非要累我们这些小的。”
他的眼泪落到我的手背上,我听见他说:“枝枝,我什么也不要了。”
他身上的荷叶香我闻着便如夏天一般。
他说,他只在见我才焚荷叶香。
我想起来了,我死命推开他。
罚月俸的那一次,召我侍寝的那一次、御花园后再见的那一次……
每一次铺面而来的,都是荷叶香。
可是,那云云呢,云云又算什么。
我想问他,可他炙热的吻让我呼吸不过来。
松息啊——当朝天子帛王。
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念头,我好像知道能活下去了。
他的苦衷,我不问,我知道他肯定有。
云云去了一年了,八月十三日是她的祭日。
我早早就张罗好了这日要用的香和祭品。
出门的时候,看到墙角的生川乌无人照料也绿油油的一片。
两个月来都是这样,早些替我煎药的宫人已被宜妃打发走了。
我也不想再吃这药。
它们还是默默地抽条结叶。
邻着的那堵院墙上的瓦片不知什么时候落了,麻雀停在上头吃食。
我细细一看,是生川乌的紫花瓣落了几片在那。
好端端的花瓣,又怎么会落到墙头去呢。
帛王日日来我这里陪我
有一日他竟穿着朝服就过来了,兴冲冲地拿着封文书就往我手里塞。
我尚是大病初愈提不起他那么好的兴头,只问他:
“什么事情那么高兴。”
正要拆手里的文书,他一把按住我的手,我不解地看他的眼睛。
他眼里亮亮的,道:
“你母亲是被陷害的,我都查出来了,如今我已派人将她安顿好了。”
霎时我便从凳子上立起来,他看见我这样更高兴了。
我拽着他的手,一遍遍问是真的吗。
“我保证,是真的,我还可以答应你,待今年年关,我带你出去见你阿娘。”
我高兴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他的嘴角弯起好看的弧度,仿佛在等我夸奖他一番。
我笑出声来,替他理了理乱了的发丝,催他赶紧回去换常服。
他扣住我按在他鬓角的手,我看到了几根白丝。
心里面又变得酸酸的,就像我见阿娘哭的时候那般。
他将头抵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我的背,说:“小栀子,我永远当你的松息。”
什么时候,他不在我面前称朕了。
我愿意当真。
松息走后,我扶着门框想惠妃。
我只是个小小的才人,没有人知道我的院子里种着生川乌。
而惠妃,正是她亲自为我寻来的生川乌的种子。
她说我身子骨受不得凉了,这味药正是难寻用来驱寒的好药。
想着想着,回过神来的时候,松息又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愣了愣,问他其余的随从去了哪里。
他眯了眯好看的眼睛,瞳孔在日光的辉映下一闪一闪透着清明的棕色。
他叫我闭眼,我照做了。
然而过了好一会儿也没听人叫我睁眼。
再睁开眼时,庭院中已无一人,我悄悄地笑他孩子气。
回屋走到梳妆台前,却看到晃着明黄的光的铜镜里映出来一朵娇白的茉莉。
我伸手从额角取下,那花浓烈地散发出香气。
我觉得我真的活了过来,从那池水里,从那茶盏里。
天气真好,从未觉得这样好过。
即便想不通阿娘为何要喂我药。
即便帛王他后宫三千佳丽。
我现在还活着,活的好好的。
我甚至愿意去相信,对云云,松息有不能说的话。
他不对我提,我便也不去问。
在我失去了儿时记忆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松息经历了什么。
六岁那年,我生了一场病。
松息爬过窗子过来看我,我不让他来,他犟着说自己身体好。
我哭闹说药好苦,我不愿意喝,他便也要和我一起喝。
大人斥他瞎闹。
他不知从哪里泡了一碗茶来,悄悄对我说,这是世上最苦的东西。
他一碗喝下去苦得牙尖打颤,小小的一个人差点栽倒在地。
我便也喝下去了那碗苦到人作呕的药。
现在看来,茶和药,都没有我过过的日子苦。
所以我喜欢喝茶,苦得人清醒。
又还要多一份我尝不到的清甜。
过了两日,我又见着了宜妃。
失了孩子,近日又不得帛王待见的宜妃。
如果她不闹着来我的清安堂的话,我还能当云云在天上庇佑着我。
我还能每天收拾一点新鲜玩意出来,攒出印在嘴角的笑意。
可是现在我不能了。
她那爱闹腾无法收束的性子,叫我想起一个人。
很远的一个人,看不清的一个人。
我想的那个人不是云云。
怎么会是云云呢。
是幼时见过的一个人罢了。
可她说她是。
她就要说她是云云。
她大笑得整个皇宫都能听得见,一字一句都砸在我的脸上,砸得我生疼。
她说:“枝栀啊,你真是好福气,你毁了我,你毁了云云!你不配叫我云云!”
我近乎要瘫倒在地,肖肖扶住了我。
她冲过来砸碎了我的耳坠子,我的步摇。
撒掉了我手里端着的青豆糕。
我的宫里头乱糟糟的,我的脑子里也乱糟糟的。
八月十三日我去给云云上香。
我还梦见了她笑着看我。
梦里的脸从脑海里引出来,对上了面前怒气冲冲的宜妃。
我才发觉宜妃藏在耳下从前用脂粉遮了的一点痣。
帛王从外面来,拦在我的身前,那飞来的玉镯子才没有直直砸向我的脸。
反而打在了帛王的肩头。
掉在地上粉碎了。
那是我在元宵夜送给云云的,盼着她能生个乖巧可爱的公主。
宜妃说,她亲手掐死了我们的雪绒,丢在了空无一人的宫道上。
购买专栏解锁剩余58%